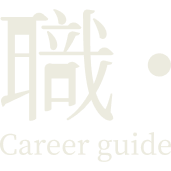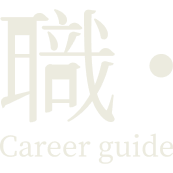薪資談判卡關怎麼辦?教你如何「把餅做大」
當談薪水卡關時,你會怎麼做?與其糾結於薪資單上的數字,不妨試試書中提供的談判協商技巧:先把餅做大,再找出雙贏的解決辦法!

![]() 文章目錄
文章目錄
許多人以為談判是零和賽局:只要我在談判桌上獲得了什麼,就代表你輸了。「一個世代以前,」《哈佛這樣教談判力》寫道:「在思考談判時,人們腦中想的問題都一樣:『誰會贏?誰會輸?』」
然而,哈佛法學教授費雪認為這種作法完全錯誤。他年輕時曾協助歐洲執行馬歇爾計畫( Marshall Plan ),日後又幫忙找出終止越戰的辦法,還參與了 1978 年的大衛營協議( Camp David Accords ),以及在 1981 年確保伊朗釋放 52 名美國人質。
最強談判技巧:把餅做大
在上述的談判中,費雪目睹不一樣的東西在發揮作用:最優秀的談判人員不會爭誰能拿到最大塊的餅,而是專注於把餅做大,找出雙贏的解決辦法,每個人離開時都比先前開心。
費雪與研究同仁寫道,談判雙方都能「贏」的概念,或許看似不可能,但「愈來愈多人體會到,能以合作的方式協調歧異。即便無法找出『雙贏』的解決方案,通常還是能達成對雙方都比較好的明智協議」。
自從《哈佛這樣教談判力》問世後,後續又有數百項研究找到支持這個概念的充分證據。菁英外交官解釋,他們在談判桌上的目標不是獲勝,而是說服另一方合作,找出之前沒人想過的新辦法。對頂尖的談判人員來說,談判不是上場打仗,而是發揮創意。
靠開放問題聽出需求
這種作法日後稱作利益性協商( interest-based bargaining )。第一步是詢問開放性的問題,接著仔細聆聽。讓人們說出自己如何看待世界、最重視什麼。即便你沒有立刻得知其他人要什麼—有可能連他們自己都不曉得,至少能引導他們也聽你說話。「如果你想讓另一方理解你在意的事」,費雪寫道:「首先要讓他們看到,你也理解他們在意的事。」
不過,聆聽只是第一步。下一個任務是處理「真正要談的是什麼?」對話的第二個問題:我們要如何一起做決定?這場對話的規則是什麼?
利用對話試探新的可能性
找出那些規則的最佳辦法,通常是測試各種對話方式,看看其他人如何反應。
舉例來說,談判人員常會做實驗—我先是打斷你,再來又彬彬有禮,接著我提出新的主題,或是做出乎意料的讓步,看看你會怎麼做;直到每個人一起決定哪些行為規範可以接受,以及這場對話該如何展開。
實驗的形式可以是提議,也可以是解決方案、意想不到的建議,或是突然提出的新主題。
不論採取哪種形式,目標都一致:試探一下,說不定能找到前進的道路。「優秀的談判者是藝術家」,史丹佛商學院教授蜜雪兒.蓋爾芬德( Michele Gelfand )表示:「他們把對話帶往意想不到的方向。」
試試提出新福利取代薪水數字
最能引發這種實驗的方法,是在討論中提出新主題和新問題,引進新的元素,直到對話出現的變化足以揭示新的可能性。「舉例來說,如果談薪水的時候卡住了」,蓋爾芬德表示:「就加進新元素:『我們一直在談錢的事,但如果不增加薪資單上的數字,改成給每個人更多天病假?如果允許員工在家工作呢?』」
「挑戰不在於消弭衝突」,費雪在《哈佛這樣教談判力》中寫道:「而在於轉換衝突。」我們所有人都會在日常對話中做這種實驗,而且經常不自覺。當我們講笑話、問深入的問題,或是突然嚴肅起來或搞笑,從某種角度來講,都是在測試同伴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邀約,一起嘗試看看。
找到共同目標與價值觀
如同利益性協商,「真正要談的是什麼?」對話能夠成功的前提,在於讓對話從爭奪主導權,轉變成某種合作、某種團體實驗,目標是找出每個人要什麼、共同的目標與價值觀又是什麼。
在外人眼裡,我們似乎只是在討論由誰負責接小孩跟買菜,但我們(參與這場安靜協商的人)都意識到潛台詞與背後的波濤洶湧,這是一場正在發生的實驗。
我們問開放性的問題(「我幫忙做這樣夠多嗎?」)與拋出新元素(「如果我負責買菜和洗碗,你負責接孩子和摺衣服?」),直到對話產生變化,足以釐清每個人真正的需求,以及我們都同意的原則:「我想尊重你的時間,工作很重要,所以如果我負責買外食,請亞文叔叔幫忙接孩子,這樣我們兩個人都能晚點回家呢?」
「真正要談的是什麼?」對話是一種協商—只不過目標不是贏過誰,而是協助每個人同意要談的主題,以及如何一起做決定。
本文摘錄自:《為什麼我們這樣對話,那樣生活?》,作者:查爾斯.杜希格,大塊文化